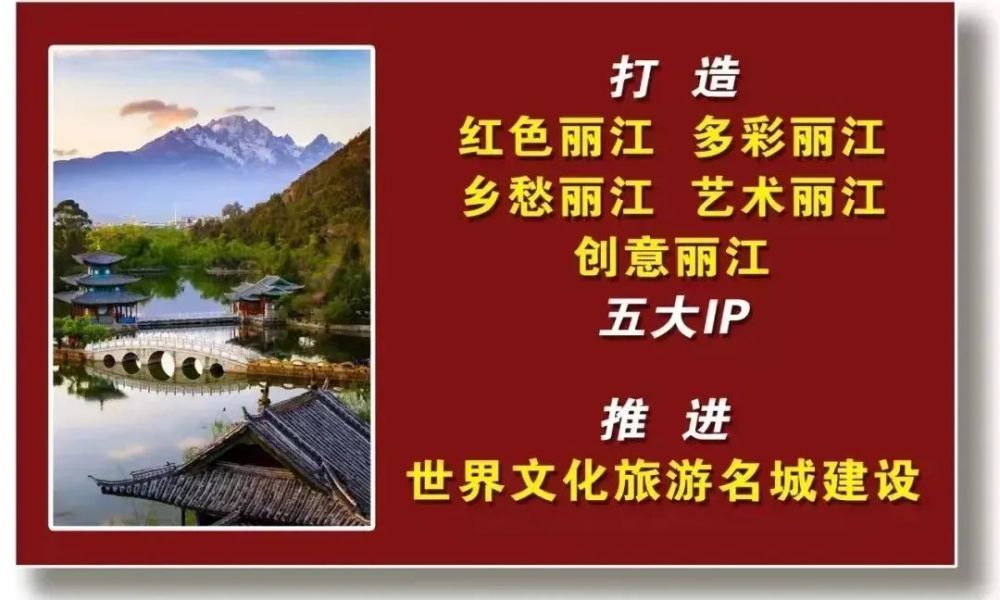
《山中逸趣序》碑考辨
楊林軍(麗江師院)
碑文概述
該碑在原麗江縣境內,今不得見。國家圖書館藏有拓片。碑通高45厘米、寬129厘米,刻于民國三十一年(1942年)。無題額,首題“山中逸趣序”,正文豎排30行,附文兩段,宗亮東隸書作跋,和清勒石。正文后兩段附文:第一段為民國三十一年萬斯年所記,共9行,內容看不清楚;第二段為校長宗亮東所題,共6行,可辨。碑文內容主要記述徐霞客通過唐泰認識木增,認為木增此人非同尋常,大肆贊美木增豐功偉業。據附文說,民國時期,萬斯年在麗江看到此文,遂刊刻在國立麗江師范學校內,以供全校師生學習。
碑文內容
山中逸趣序
余往交唐大來,侈談金碧蒼洱之勝。其中苞異孕靈,問出而生名世。譽滿四裔,海內遙瞻,如霱云曙星,不見其人,而愿見所著述,若生白木公之《云薖集》,業行世久矣;此《山中逸趣》,又大來所手訂以傳者也。公世祚封侯,晉修藩伯,以雄武一軍,成斬馘之功,為飛將。以金貲數萬,佐軍興之急,為忠臣。以威望九鼎,落番夷之膽,為良翰。無事則詩書禮樂,有事則戎馬行間,何自暇得逸于山中也?公閉意榮祿,蚤謝塵縷,學老氏之知止,同孔明之淡泊,如李西屏有子愬,吳武安有子拱,智足知兵,才堪八面,以雅鎮石門鐵橋,丸泥可封;使金沙之涯,儼標銅柱,無疆事之憂;故疏辭五上,天子特金幣褒嘉,方許謝政。公得練巾野服,容裔于松庵雪洞中;環碧掃青,皆山也,但公世著風雅,交滿天下;征文者,投詩者,購書者,以神交定盟者,嚶鳴相和;聲氣往來,共中原之旗鼓。銀鹿青猿,走山中無虛日,公獨領山中之趣于逸,有賦、有篇、有吟、有清語,拈題命韻,高矌孤閑;煙霞之色,撲人眉宇;讀之,猶冷嚼梅花雪瓣也。雖然,公之逸,豈僅浪漫者;性喜博綜,而樵獵于蝌漆烏鉛,類陸澄劉峻。繼雪山玉水之音,而接武于祖孫父子之作述,類韋弘景薛元超。精研典釋,悟入宗乘,如作家禪客,類張無盡蘇子瞻。是總以有余之才,與無所用之力,倍勞而得逸,因逸而成趣;讬圣世之逸民,作衣冠之巢許,非有綆瓠絲竹以娛聲伎,文異錦以御鮮華;孹鱗酢龍以來奇嗜;惟椰瓢蘆被,煨芋餐芝,人不知其為世臣享世祿者,洵足稱山中人也。吾師乎!當讀名山記,李景山有句云:“麗江雪山天下絕,積玉堆瓊幾千疊;足盤厚地背摩天,衡華真成兩坵垤。”有山如此,公得逸于山中,非有神仙福者,豈易知山中之趣哉!是篇也,補記名山可矣。
大明崇禎霞客徐宏祖題
附文第一段不清晰。附文第二段的內容如下。
三十一年秋,國立北平圖書館萬君稼軒來麗政察,將木氏珍藏徐霞客先生遺書“山中逸趣敘”勒諸貞珉,留校以垂不朽。全校師生至深欣感先生遺書如旨,光羽胄。甚珍貴,后之來者當景仰前賢而彰之。
國立麗江師范學校校長宗亮東謹識
石工和清勒石

玉龍雪山。
碑文考辨
關于這段歷史的真偽,需要回溯到《徐霞客游記》中來尋找答案。據《游記》記載:徐霞客到解脫林的第三天下午,“大把事來求作所輯《云薖淡墨》序。初三日余以敘稿送進,復令大把事來謝。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《云薖淡墨》,繳納木公……其所書洪武體,雖甚整而訛字極多……”就這段史料而言,前后皆為一本書,為何徐霞客寫序后又說“訛字極多”呢?顯然,這說的是不同的書,只是把書名弄錯了。查看相關史料才發現,第一次送來的是《山中逸趣》,第二次送來的才是《云薖淡墨》。
徐霞客在《游記》中說為其作序,并流傳于世。然而從徐霞客所遺留的文書來看,沒有序,倒有一篇跋。關于徐霞客所寫的跋,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流傳有兩篇。其中一篇如是說:“公世著風雅,交滿天下。征文者、投詩者、購書者、以神交定盟者,嚶鳴相和,聲氣往來,共中原之旗鼓……生白木公示《云薖集》,業已行世久矣;此《山中逸趣》,有大來所手定以傳世者……公閉意榮祿,早謝塵纓,學老氏之知止,同空明之淡泊……故,書辭五上,天子特金幣褒嘉,方許謝政……銀鹿青猿,走山中無虛日,公獨領山中之趣于逸,有賦、有笛、有吟、有清語,拈體命韻,高曠孤閑;煙霜之色,撲入眉宇;讀之,猶冷嚼梅花雨瓣也。”這很顯然是一篇獻給木增的頌歌,通篇充滿阿諛奉承之詞,被認為“可以作為木增傳略看”。
從落款“宏祖”2字和內容來看,這顯然不是徐霞客的文章。理由有:其一,徐霞客字弘祖,由于清乾隆皇帝名弘歷,為避諱改為“宏”字。從徐霞客所作的文書時間來看,不應該改字,只可能是后人所為。其二,序與跋,都是評價該書緣起、作者特殊的經歷、書的特色以及歷史地位等方面的文體。序一般放在文章前面,偶有放在后面,也要取為后序,而跋都放在文章的最后。徐霞客看到此書時,已有唐泰等人作序,并已編訂成冊。本來像徐霞客這樣的文賢,作個序不為過,但只作了個跋,便于編訂,也體現了徐霞客的謙虛。其三,從文風和內容看,大有歌頌木增之豐功偉績,這與徐霞客一貫的為人之道相悖。因此,徐霞客給《山中逸趣》寫的是跋而不是序。方樹梅先生由于沒有看到徐霞客的真跡,便認為是徐霞客為人寫的序,“海內殆無第二篇”。
其實,此跋是徐霞客在麗江為木增的詩文集《山中逸趣》撰寫的一篇佳作。此文在流傳過程中被一位清代貢生篡改,把章臺鼎所作的序署名為徐霞客。這樣的嫁接,看似可以以假亂真,想不到有多處破綻。后經數位專家多年來的不懈關注和考證,云南大學朱惠榮教授對此考究最勤,專門撰寫了萬余字的論文以辨明是非,扶正彎曲。當然也有人認為,此文有章臺鼎借徐霞客之名來揚名之嫌,其實這樣更是冤枉了章臺鼎。現在,清代貢生所作的“贗品”已恢復歷史的本來,實為一件令人“逸”樂之事。
《山中逸趣》是木增的一部詩賦集刊,收錄有賦2篇,詩194首,是木增的得意之作。于崇禎十年(1637年)唐泰為此書作序,后來章臺鼎、梁之翰、徐霞客等也分別為之作序或跋。徐霞客所作的《山中逸趣》跋,共有546字,用篆體書寫,從風格和行文上與章氏截然不同。現以徐霞客所作的原文為底本,參考朱惠榮教授所著的《徐霞客與〈徐霞客游記〉》以及余嘉華教授所著的《木氏土司與麗江》相關內容,全文摘錄如下。
山中逸趣跋
自兩儀肇分,重者為地,重之極而山出焉。以鎮定之體,奠鰲極而命方岳,但見其靜秀有常而已,未有能授之逸者。熟知其體靜而神自逸,其跡定而天自逸。彼夫逃形滅影,塿坯湮谷,曾是以為逸乎,穸直與山為構者也。進而求之,伊尹逸于耕,太公逸于釣,謝傅逸于奕,陶侃逸于鬲,逸不可跡求,類若此而大舜有大焉。其與木石居、鹿豕游者誰,其逸沛然決、莫能御者又誰。跡野人求之市,復跡大舜求之不得,是所謂真逸也。千古帝皇,莫不以舜為兢業,自乃鼓琴被袗,其得力于深山者固趣。但自有虞以后,山川之勞人亦久矣。神禹以之胼手胝足,秦人因之驅石范鐵,焉睹所謂逸。乃麗江世公生白老先生,夙有山中逸趣者,何非天下皆勞而我獨逸?天下俱悲,而我奚趣?即以天下之勞攘還之天下,而我不與之構;以我之鎮定還之我,而天下陰受其庇。與山之不能相忘,我欲跡之。是山非天下之山,乃我之能鎮能定之山也;多山非我一方之山,乃天下之山,而為鎮能定之山也。故,文章而粗石者,逸為出岫之卷舒,云影而飛絮者,逸為天半之璚玉;泉靜而濫觴者,逸為左右之逢源;丘壑而宮商之音,逸為太始賦形;而金石之宣,逸為均天。先生此集所以卷綸藏密者,與莘渭各異而鎮意念之心,故悠然跡外,即納之大麓,又何與于舜庭之揚歌。垂承則能赍天下于春臺者此趣,能翔太和于寰宇者此趣,而山中云乎哉?然必系之山中者,所以奠鰲極而?方岳也。弘祖遍覓山于天下,而亦乃得逸于山中,故喜極而為之序。
崇禎己卯仲春朔旦
江左教下后學徐弘祖霞逸父頓首拜書于解脫檀林

群山。
徐霞客所作的《山中逸趣》跋,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跋,而是一篇借題闡述天地變遷、人情世故的精華篇章。徐霞客不愧為地理學家,用地學眼光和思想觀察山川變遷,承認地殼運動是地表凸凹不平的原因。“重者為地,重之極而山出焉。以鎮定之體,奠鰲極而命方岳”,“彼夫逃形滅影,塿坯湮谷,曾是以為逸乎,穸(是)直與山為構也。”隨著人類不斷參與地表形狀改變,因而就有了“自有虞以后,山川之勞人亦久矣。”
接著,他抒發了自己游歷山川30年來所積累起來的深邃的哲理。運用運動與靜止的觀點,“見其靜秀有常而已,未有能授之逸者”“孰知其體靜而神自逸,其跡定而天自逸”,這就是說,“體”“跡”決定“神”“天”,講到人世間的和諧問題。“以奠鰲極而命方岳也”,從表述自然變化規律轉入人世間,“進而求之,伊尹逸于耕,太公逸于釣,謝傅逸于奕,陶侃逸于鬲”。至此,他道出了自然界與人類一樣也需要保持和諧,方能找到“逸”即平衡,一旦失去平衡,人類只好改造和防御一些自然變化,“神禹以之胼手胝足,秦人因之驅石范鐵,焉睹所謂逸。”大禹治水,三過家門而不入,因為常年接觸水,手腳掌都長出一層厚厚的老繭;秦國人壘起石頭,再鑄上鐵水以防水患。這些怎么能說是“逸”呢?
筆鋒一轉,他談起木增的生活情趣。“夙有山中逸趣者何?”徐霞客結合木增戎馬半生的經歷,說明木增并非逃離人間世事而避居山林,“非天下皆勞,而我獨逸,天下俱悲,而我欲趣。即以天下之勞攘還天下,而我不與之構;以我之鎮定還之我,而天下陰受其庇”。袁宏道在《敘陳正甫會心集》中言:“人所難得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,水中之味,花中之光,女中之態,雖善說者不能一語,唯會心者知之。”木增也好,徐霞客本人也好,祖國大好河山并非為某人所獨占,而是“是山非天下之山,乃我之能鎮能定之山也;多山非我一方之山,乃天下之山,而為鎮、為定之山也”。道出了徐霞客同木增共同情趣和愛好,知己難求!木增也曾作詩曰:“我愛芝山景最佳,屢經甲子不思家。此中飲食殊人世,辟谷常吞日月華。”
自然界和人世間有眾多和諧的景象。“文章而觕石者,逸為出岫之卷舒,雪影而飛絮者,逸為天半之璚玉;泉靜而濫觴者,逸為左右之逢源;志情而宮商之音,逸為太始賦形;而金石之宣,逸為均天。”也就是說,“各美其美”方能找到事物存在的合理之處。木增的大作《山中逸趣》表現出了“卷綸藏密者,與莘渭各異而鎮意念之心,故悠然跡外”。這么好的文章可與天高地淵作比較,它本身就具備了這樣的內容和精神。“然必系之山中者,所以奠鰲極而命方岳也。”道出了只有有心人才能知道這些自然變化。最后,徐霞客很委婉地道出了一生的行世準則和心靈深處的向往,“弘祖遍覓山于天下,而亦乃得逸于山中,故,喜極而為之序。”
此跋道出了徐霞客在半生游歷中的深刻感悟。因此,此文不如說是徐霞客對自然、人類活動規律作一次“表白”。對明末社會動蕩不安、民不聊生作了暗示,并指出了處理辦法:“千古帝皇,莫不以舜為兢業,自乃鼓琴被袗,其得力于深山者固趣。”體現了一位看似不聞政事的游客,實則是關心民事、呼吁社會和諧的社會活動家。
此文能有如此深刻、富有深邃哲理的跋,確實體現了徐霞客與木增都是好山水逸趣之人,有著共同的情趣。因而,從一個側面道出了徐霞客不虛此行的感慨溢于言表。納西族土司木增在邊遠之地能有如此的感悟,徐霞客深為其動容,故而作此文以示后人。
說句題外話。當年萬斯年以為這是徐霞客的真跡,推薦給時任國立麗江師范學校校長宗亮東,后者用巨石刊刻后立于校園供全校師生學習。做這件事的出發點是好的,結果卻造成錯訛。
圖片由周侃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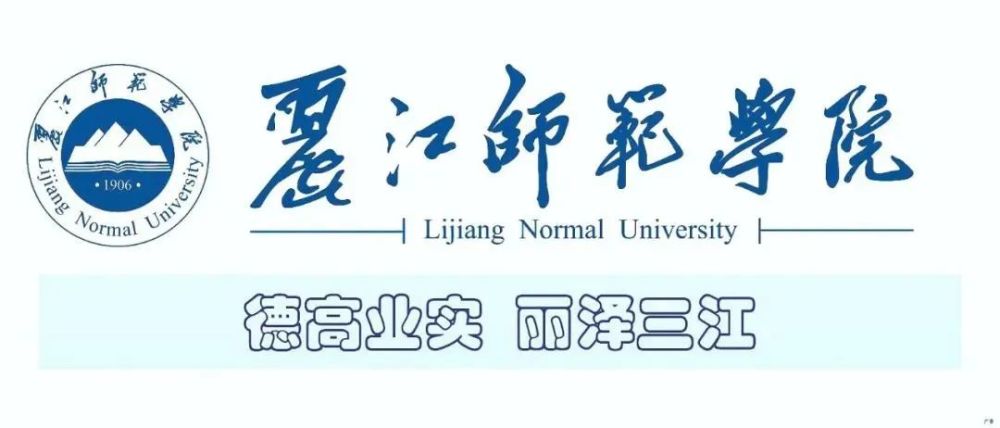

編輯:白 浩
校對:張小秋
二審:和繼賢
【聲明】如需轉載麗江市融媒體中心名下任何平臺發布的內容,請 點擊這里 與我們建立有效聯系。